-
(測試)【完整菜單】延長至五月底!添好運港式飲茶 100 分鐘點心吃到飽只要 699 元
2025-04-28 12:44 -
美日俄三巨頭如何瓜分世界是我們該擔憂的事
2025-02-22 07:00 -
廖偉棠專欄:《巴布·狄倫:搖滾詩人》──挑釁的傳主,不挑釁的傳記片
2025-02-22 07:00 -
台日菲防禦監控情資共享之必要與迫切
2025-02-22 07:00 -
為什麼川普不可能變獨裁
2025-02-21 07:00 -
國防部修訂「志願士兵甄選條件」的省思
2025-02-21 07:00 -
這樣的信徒不是在敬奉神明
2025-02-21 07:00 -
【大師講堂】抗中或成川普和莫迪「兄弟情」的催化劑
2025-02-21 07:00 -
從台灣到美國 政治文化才是民主良窳的關鍵
2025-02-21 00:00 -
「藍白敵人論」無法讓罷免運動成功
2025-02-20 07:01
一副假牙-施明德回憶錄《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之三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對我都是一個重要日子。是我的另一個政治生命的生日。被捕後我就進入死亡暴風圈,起訴二條一正式進入死亡邊緣,宋景松先生被槍決時我已準備好擇日步上斷頭台了。為甚麼我會被判無期徒刑而非死刑?連那個心不甘情不願宣讀判決文的主審法官成鼎,一定也不知道為什麼只判我無期徒刑?他們的劇本在槍决宋景松先生時一定不是這樣寫的。
我的生死簿被改寫了暫時沒有被殺的可能了,我本該有個平安之夜。但是這一夜我反而不僅難以安眠,還思緒非常活躍。童年的記憶一一重還,生命翻轉過來品味。死囚們都走了,為什麼上帝還獨留我活在人間?我檢討我的辯護策略,辯護內容,尤其死生哲學。我是個凡事會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思考檢討的人,這次我認為假牙是個關鍵,左右我的死生判決。
我自然又回想起保安處那段刑求的日子……。
特務們都不説自己的名字和官階都自稱法官,我只能從他們的口音分辨是那裡人。因為從進入軍校到分發部隊的幾年中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都是中國各省的軍人而且鄉音都很重,這樣的環境讓我學會從每個人的發音中分辨出他們是哪一省人。偵訊的小組有時五個有時兩三個,他們中有浙江人老國特,有廣東人、福建人、湖南人和打手四川人。年齡都在四十幾到五十出頭,全不穿軍服。
我被移囚保安處不久就被提訊到隔離的偵訊室。特務從一開始就不相信我這個才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怎麼可能有這樣宏大的思想,會這樣堅決的追求理想與信仰?他們都非常看不起臺灣人認為臺灣人只會為權為利出賣自己,要不就是被人收買利用。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逼出我們背後的領導人,擴大案情。那時我完全不知全案已經抓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他們都已經被起訴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了。那個一口浙江腔但郷音不像蔣介石那麼濃,又高又斯文顯然是頭頭的特務一開頭重點就是追問我背後的領導人是誰?我獨囚偵訊室一個月的目的就是要逼問這一點。我知道他們如果能從我口中逼出這個﹁大人﹂,他們口中的大人,他們就釣到一條大魚就能建立一個大功。
我真的說不出哪個﹁大人﹂,因為真的沒有。在疲勞審問的時候,我曾暗自思量他們可能如何刑求我。在馬明潭的看守所同房已告訴我他們被刑求的各種花樣,到東本願寺我也看到被粗暴打到鼻青臉腫,腹背瘀青,尿不出來的小琉球老船長老仁。還有被刷陰道從外表看不到傷痕的林滿好。楊仁保、嚴君川都還只是疲勞審訊,被罰老虎蹲跳、用三隻筷子夾手指或用一根童子軍棍夾在膝蓋內側逼他們下蹲……,這類小把戲。我在金門第三招待所已經品嘗過老虎蹲跳,不過是小菜一碟碟。我猜想,他們大概也只會對我玩玩類似的手段,讓我受點皮肉之痛。我肯定他們不敢下重手。我確信特務不敢對人犯刑求致死,人犯真死了特務也不是好缷責的。
所以當特務頭子命令我站起來仔細想想再説出﹁大人﹂時,我一點防備都沒有就是輕鬆地站著,偷一點疲勞審問中的﹁休閒時刻﹂。當特務從背後猛然突襲時,刹那間我就像一尊瓷器人偶般重摔倒在地上,顏面直接著地,第一時間那個像流氓的四川佬特務還沒有看到我的正面上下牙已掉了八顆,又繼續踢我,直到他們看到滿地血跡,白臉特務老廣才出面阻止……。我才看到那支撞擊我的槍托還包紮著很厚的布墊,顯然他們並不真正要讓我致命。
見血了,白臉特務立即喊停還趕快叫人端臉盆替我拭血,拿清水讓我漱口……。
有了明顯外傷,目的又沒有達到,我就這樣繼續被留置在偵訊室追問﹁大人﹂,沒有送回原來的押房。他們把我徹底孤立隔絕起來。他們大概想才打掉我八顆牙齒死不了人,沒有想到我整個口腔開始發炎,牙床全紅腫疼痛不堪,太陽穴抽搐像無數細針扎刺,頭部終日脹痛。如果他們就此停止折磨我,用心醫治我,八顆假牙的形狀還不致於太恐怖。但這個時候特務的邪惡之心卻很可能反而救了我,讓我日後在辯論庭可以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反擊。他們找來軍醫替我塗藥,我不覺得是真心治療,讓我整天持續難過,我聞到自己的嘴巴發臭苦澀。特務跟我講話都不敢太靠近我。
專門扮白臉會講潮州腔閩南話的老廣特務除了安慰我,給我溫牛奶、豆漿,三不五時一樣會反覆問:﹁你們的老闆是誰?郭國基?郭雨新?李萬居?高玉樹?李源棧?﹂後來還指明:﹁對,是省議員李源棧,他兒子和你哥哥很熟。﹂
我否認,湖南佬就接口:﹁我們是有情報來源的,不是寃枉你的,說出來嘛沒有關係的。坦白從寬,說一個就好了。軍人嘛,頂天立地,敢做敢當。﹂
 施明德過去兩年閉門寫作,完成17萬字的回憶錄第一冊《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攝影:王怡蓁)
施明德過去兩年閉門寫作,完成17萬字的回憶錄第一冊《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攝影:王怡蓁)
掉了那麼多顆牙齒,講話已很不舒服,事實上我也真的招不出來。沒幾天浙江特務頭子就叫牙醫進來,﹁他說牙齒很痛,幫他處理處理一下。﹂
牙醫看了看:﹁牙齒都鬆動了,不快拔掉發炎更厲害了,就麻煩大了。﹂
特務頭子拿出一張已備好的字條,上面寫著:﹁我的牙齒舊疾復發,自願請求治療。﹂要我簽名才給治療。
要我簽這張字條,是不是將來拿來辯解不是他們打掉我八顆牙齒的?我一下子沒有仔細思考,因為真的太疼了,我就簽了。特務讓我坐在他的有扶手靠背的椅子上,就讓牙醫替我拔牙了。軍醫是有打麻藥的動作,但針筒裡是否有放足夠的麻藥呢,天知道,事實是每拔一顆都讓我痛到剉點尿水,根本是整人的手段。我能忍痛是出名的,盲腸炎可以忍到惡化成腹膜炎。我能忍痛不是天生的特質,是這樣一步步被磨練出來的。
這次軍醫拔了六顆。邊拔,浙江佬就在旁邊說:﹁施大觀測官,你們只是被人利用了,不是我們的敵人。招一個就好了,你的責任也會減輕,招兩個,保證放了你。蔣總統可是賞罰分明會論功行賞的領袖。蔣總統、蔣主任訓示我們,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萬惡的共匪。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我們都完全效忠領袖。﹂
偵訊室空蕩蕩,除了幾張椅子,一張沒有抽屜的桌子,牆壁上掛著一張穿著中山裝微笑得很慈祥的蔣介石照片。這個慈祥的老人正微笑地觀賞我的苦難。
特務的特質是對獨裁者絕對的忠貞,這是他們幹盡傷天害理的勾當還不會自責的原因。就像艾希曼對納粹希特勒。
特務也許正等我喊停,喊不要拔了。我張著大口緊閉雙眼,屏住呼吸,每一根手指牢牢抓住扶手一邊剉點尿,強忍下來了。耳朵還得忍受特務恥笑我:﹁哎呀!你一點都不像革命軍人,拔顆牙就尿褲子啦!﹂
從被打掉牙齒,這次又拔了六顆,兩邊太陽穴天天抽痛,兩頰鼓腫,吃消炎藥讓胃隱隱不適。晚上止痛藥效退了,叫特務再給止痛藥他們都裝作沒有聽到。嘴完全無法嚼食東西,每天只能把饅頭泡在豆漿或牛奶中,攪成泥吞下去。嘴裡太澀了,就舔一小塊豆腐乳。
刑求,對一個真正的反抗者是種最嚴酷的磨練,也是反抗者的高級在職訓練。刑求的功能是會擊碎了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讓反抗者從心底產生赤祼祼的敵意,讓敵我意識和攻防策略油然全面啟動。當然,有些被刑求者也可能因刑求而全面崩潰,讓特務予取予求。反抗者必須獲得前人的經驗,刑求最難熬的時刻就是當下。這時的疼痛、恐懼、懷疑、憂慮都會一起湧起摧毀了你。如果你熬過了,你
就有機會成為一個人!記住那個﹁當下﹂,會是度秒如年,會高度懷疑自己的堅持,更常常會令你萬念俱灰盼求解脫。如果你放棄了,就會俱往矣,永遠不會有歷史的明天了。
整個口腔疼痛加背痛,睡在偵訊室的行軍床上很難入睡,我請求特務晩上讓我睡在地上。偵訊室晚上是從外鎖著的,有獄卒整夜監視。天仍然炎熱沒有電風扇,當然更不會有冷氣,海綿牆吸熱,地板反而是唯一的涼源。但躺久了汗會黏地板必須轉側或移動位置。每次移動聲響獄卒就緊張兮兮地進來察看。但是當被痛醒沒有止痛藥,叫獄卒再給止痛藥他會說要報告長官。然後就沒有下文。這時只能靠冥想,集中注意力想往事,努力摒棄痛感。這樣的冥想或回憶會讓自己的思想四處流竄,有一夜腦中突然閃現應該收集刑求證據的念頭!
通常刑求都會船過水無痕,這是特務的專長,刑求犯人要有效要避免致命又要不留下痕跡。小時候爸爸被釋放後已不良於行,但人放回來父親認為能回家一切就算了,也不敢再計較。事實上,計較也沒有用。在馬明潭的自治員刑警談刑求都說特務一定會設法抹掉所有證據。在這裡同房的小琉球船長老仁被打到扶回房小便都尿不出來,全身瘀青。兩天後就能走路了,傷痕不久也會消逝。只要傷痕還在,特務就不會移送法院。反正要拘留多久是特務決定的,雖然刑事訴訟法和軍事審判法都明文規定,拘押一期兩個月,得延長一次,也就是說特務依法只能拘押四個月,不起訴就得釋放。但是警備總司令部的特務才不管這一套。不,不只警總的特務,調查局、軍情局、刑事警察單位凡捉政治犯的機構都一樣,阿保、老仁船長,還有嚴君川被關在這裡都快半年了。他們有傷痕也早就消失了。還有同房基隆人阿保仔,楊仁保的同案叫林滿好的女走私嫌犯早上被提訊,晚上是被兩個女特務架著回房的。因為她被特務用牙刷刷陰道,刷到流血痛到不能走路。但過幾天陰道也會復原,又能走路了,事後當然也驗不出傷痕拿不出證據。
﹁被打落了牙齒呢?應該可以呈庭作證。但是牙齒都在那個白臉特務的手中他真的會還給我作紀念嗎?如他所說的?如果做了假牙呢?﹂我這樣自忖。這是漫長囚禁生涯中我第一次發現獨囚的好處,讓囚人可以做深度的思想,反覆辯證,不受干擾。

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會被判死刑,這種蒐證的念頭只是讓自己更勇於承受痛的滋味而已。但是有了這種呈庭作證的念頭後,幾天後特務再叫軍醫過來檢查了我的口腔,軍醫說情況更糟時,我就默不作聲了。特務仍糾纏我的背後大人是誰?顯然這是他們唯一想要的。他們備好一份筆錄明確指出﹁大人﹂就是省議員李源棧,還説是透過李源棧之子李日煌和三哥施明雄的同學關係牽上線的,並聽從李源棧省議員的指揮。特務要我簽名。
我不肯簽,不是我逞勇不招也不是我比別人英勇,那時我還只是一名年輕軍官沒有受過特務訓練自己也沒有自我訓練過,我招不出來沒有招只是因為確實沒有這種事。不像八年後﹁泰源革命﹂失敗後,兩度被偵訊不管特務們怎麼提詞,怎麼誘騙威脅我都堅持﹁不知情,沒有參與﹂!完全拒絕招認,那是我已經是個嚴格自我訓練過的革命者,深知我一旦招認知情參與,不只自己沒有活命更會扯出一大票同志的死亡。
湖南騾子特務看我不招就拿出一份寫著:﹁本人因牙周病經醫生診斷病情嚴重,本人自願拔除牙齒以維護生命。一切責任自負。﹂其實這個時候我的牙床的疼痛已比日前好多了,我不覺得有再拔牙的必要。我不知道這是特務在威脅我,還是要我主動拒絕再被拔牙治療,以便又討價還價。何況我已經簽了一張了,為什麼還要我再簽一張類似的求醫字條?也許是前次的字條只寫治療,沒有明確寫拔牙,這份要明確寫上﹁拔牙﹂他們才好為刑求脫罪自保?敵我意識讓我處處攻防中。
這一次我一提筆很乾脆就簽了,反正已剩下沒幾顆牙了,加上將來可能要呈庭做證據的念頭已經形成,忍耐力就增強了。雙方各懷心機,鬥智又鬥耐力。從此我就任由牙醫拔牙了,麻藥依舊遠遠不足,我又每每還會痛到剉點尿!
特務頭子每次牙醫進來時都會跟進來關切病情,是他叫牙醫進來的還是牙醫知會他的?我不知道。我的牙周病真的嚴重到必須一再拔牙嗎?我也不知道。但每次他都會不斷在旁嘮叨:﹁說出背後大人是誰?坦白招供對大家都好,不是拔光了牙你就躲得過,我們一定有辦法叫你老實地說出來。是你自願簽了字要我們醫治你的牙周病的,我們沒有責任。我們沒有刑求你。﹂
原來特務真的已想好應付法庭或外界的藉口和證據了,有了我簽了名的字據在他們手中,他們更肆無忌憚了。奸詐邪惡是特務的特質。但是我的背後真的沒有大人。特務點名的大人都是政客型的人物,在我看來他們只會在安全範圍內提出一些改革的言論,不像我們是要捨命為臺灣爭自由爭主權,結束外來殖民統治的。這是政客和革命者、反抗者最大的差異。我才不可能配合特務亂咬人,我若招認他們為頭頭是汙化了我們的理想性,那時年少輕狂。輕狂是反抗者絕對必備的。
這段在保安處偵訊的獨囚日子對我是肉體的摧殘,更是心靈的折磨。孤立、隔絕、不安、焦燥、憤怒、軟弱、絕望、高昂…種種情緒都曾短暫交加佔領我心,又會莫名的消逝然後又無端地出現。特務進來立即全神備戰,像鬥雞場已被啄傷得體無完羽的鬥雞仍然得展翅掩飾自己的脆弱;有時聽到﹁白臉﹂特務幾句安慰的話語,就必須泫然淚下流露感動和脆弱的一面讓對方覺得我很真誠…。有時
兩三天特務完全不聞不問,只有伙伕兵送進流質食物和飲水,我竟然會向門外警衛表示要求見特務。開始特務以為我想通了要招出背後的﹁大人﹂興奮地進來,結果發現我竟然只是因為沒有人對話孤獨到只想跟人說話而已,就悻悻然帶著怒氣而去。特務一定看多了獨囚人的百態,也知道利用獨囚取供的奧妙。所以我懇求給我書或筆紙讓我寫信,特務都完全置之不理,讓我處在徹底孤立單調的空白中。這樣日復一日他們盼望看到我會有什麼變化……。白天我會在恐懼和期待的矛盾狀態下等待特務的身影,傾聽任何聲響分析可能出現的後續狀況,精神總是處於緊繃的狀態。黃昏之後知道特務今天不會再進來了,如果顏面神經會抽痛,脊椎會劇痛,我還能集中精力和疼痛糾纏作戰讓自己有點事情可以做。有時痛感短暫消逝或痛感減弱就感到無聊丶空白、虛無、孤獨到不知如何自處,在小囚房內踱步,無意義地細看海綿牆壁紋路和釘工會量量工人切割是否均勻…。當有意識地發現偵訊室內連一隻蚊子、蒼蠅都沒有,竟然會把饅頭屑屑放在門縫處盼望引誘螞蟻或蟑螂從門底縫縫鑽進來,人就趺坐地上呆視許久……。回憶,這個時候就常成為不速之客,成為親密的愛人填補空白和孤獨,讓自己不管是在狹窄囚室內踱步或臥倒、斜背牆壁都不再有那麼強烈的孤單感。
孤獨中回憶是亂竄的,不必然有因果關係。你不會預知過去的什麼片斷會突然湧現,除非刻意。亂竄的回憶多是和悲慘的現況相呼應的,此時此刻這類自怨自艾的回憶最容易竄埸但它是有害的,只會使懊惱更懊惱,使後悔更後悔,使軟弱轉為頹廢,使恐懼淪為無恥之心。當我驚覺這種本能式回憶的墮落性,我就開始讓意識性的回憶來排除孤立感。我一再召回美好往事與我作伴,像童年時光與家人相聚的點點滴滴,美食美景,童年的稚戀,性愛的激景…都暫時讓我從孤獨中解脫,但門外一點點聲響會立即引我注意而中斷這類回憶。當我再度回到孤零零的現狀時,取代的就會是強烈的惆悵感,因為落差太大。我發現這類風花雪月的追憶無助於面對冷酷的當下。幾度體會後我開始有意識地召回二二八事件中在火車站前端槍進攻車站高中學生們的影像。他們是那麼勇敢地反抗新來的壓迫者,一個倒下又一個奮起。鮮血就這樣在馬路上一灘灘地像血花,拖曳下的血跡彷佛是在向我們這些偷窺到現況的後生晚輩指引方向…。這類回憶會像強心劑那樣給我力量。這些孤獨的無聊時刻腦中還常常會出現二二八事件平息後,被押解跪在卡車上背後插著名牌全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的反抗者,最終一一在高雄火車站前三角公園被射殺的壯烈情景……。這類有死生有鮮血的回憶,竟然像服用了安慰劑般能令我平靜的入睡。就這樣,像二次大戰中躱防空洞任美軍轟炸和在小金門﹁單打雙不打﹂的聽憑砲彈轟襲的往事也一一重臨,很奇怪這時追憶中的往事連細節都格外細膩清?……。我發現這類回憶的重量和厚度在慘遭刑求後的孤獨中才是相襯的。浸淫在這類往事時,蹤然被中斷再回到現狀,心中也不會有沮喪的感覺,反而像上了一堂心靈輔導課般有飽足感,有鼓勵作用。就這樣在那二十幾天中,我覺得自己的心智成熟是以倍數在發展。滄桑指數超越常人被訓練所需的蹂度不知高出多少倍,也許這就是讓我一生都比我周遭的人更具抗壓力的養成過程吧。
在遭到暴力刑求後,我又這樣承受相當時日獨囚的煎熬可能得到特務們的認可,相信我背後沒有更上級的指使者,等到我口腔內的傷口癒合得差不多了,他們才讓我回到原來的押房。
後來我們在保安處會繼續多待了半年之久,就是在等替我做好假牙,我都沒有再見到那幾名特務,也沒有再被提訉。這段日子我的同案張茂雄等人也沒有被偵訊。他們被移送保安處好像只是過水一般。他們就是被丟在那裡不聞不問。戒嚴時代他們想怎麼關你,關你多久都是隨他們的意思的,法律的規定完全不起作用。特務只要有一點點懷疑,他們就可以任意收押、偵訊、刑求、長囚、羅織…。
以苦難來說,拔牙的痛只是一時的短暫的,最惱人的反而是那槍托的一擊誘發了我的遺傳疾病僵直性脊髓炎。這種疼痛延續了二十幾年,嚴重時連呼吸都會牽動全胸部的痛感神經,打噴嚏時整個背部與胸部的每條神經都會被抽緊劇痛。夜裡必須半躺半靠著睡是常事,而且是天天的,尤其快天亮時刻。但是這個疼痛也成為自我磨練的老師,我每天都忍痛強求自己必須動,必須挺直,不准自己為了避免疼痛而蜷曲身體,我決心不斷與它在對抗中共存。因此反而讓我直到今天仍保持挺直的體態,還有相當靈活的頸椎、胸椎和腰椎,連醫生都覺得意外,完全不像其他僵直性脊髓炎患者。
時間拉長之後,更痛的已不是拔牙之疼也不是脊椎之痛,而是心慟。保安處的這段遭遇是我一生中最不想追憶和訴說的,還常常努力要淡忘的。每次回憶不只是那種痛感會重現,還會呈現那個不知所措的臨場感。特務們進來,不知道他們又要使出什麼手段,他們出去了會自忖他們又在研究什麼花招?空無一人的偵訊室是厚厚海綿的隔音、防止撞牆自殺,卸下門的廁所一覽無遺,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某處監視著我。二十四小時都在充滿敵意的注視下孤立、徬徨、恐慌、無助的感覺緊緊纏身。每一天都覺得自己彷佛置身於樹蔭濃密的原始森林中處處有豺狼虎豹環視,腳前盡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百步蛇、響尾蛇、龜殼花在蠕動……。這樣無情殘忍的經驗,一生一次就夠了。每次追憶就是另一次的折磨。恨,就會再滋生,我不想讓它鑄成一座心牢……。這是我的善良也是我的幸運,我不想用恨待人,也不想用恨自戕自囚。恨的力量強過愛。恨能使你法力無邊對抗一切逆境,但它像兩刃刀能傷人也能傷己,而且後遺症無窮。愛,如春風如暖流,不會強烈卻持久永恆。坐牢人只能靠愛活下去。靠恨活下來的人,終究會傷自己傷到不成人形。
宣判後,情緒高度亢奮的這一夜我回憶起這段過程,我聚焦思索的卻是保安處為什麼沒有在辯論庭後把我簽了字﹁我罹患牙周病請替我拔牙齒治療﹂的兩張證據拿出來反駁?為什麼?
如果我一到軍法處看守所就像其他政治犯大聲抗議刑求或大剌剌地寫在答辯狀上,驚動了特務,特務就有充裕的時間研究對策以求自保。那樣,他們應該就會拿出那兩張我簽了名的字條找出用什麼藉口來反駁解釋缷責,法官依例就會載明在判決書中替特務解套。我已看到他們對所有的刑求控訴都是這樣應付的。軍事法庭的審判過程都是如此結局。我沒有看過一份判決書中法官敢寫下被告被刑求的判詞!證據在什麼關鍵時刻提出事關成敗。我能忍,忍到辯論庭媽媽也在場時,才出其不意公然在眾人面前亮出來,使他們完全措手不及。我認為他們如果拿出我簽了名的求醫字據,一旦公開討論、對質,案情過程就會全曝光,破綻一定更加百出,包括宋景松已被槍殺的全案案情。獨裁者殺人除了要肅清敵人就是要製造恐怖氣氛,但他也不想讓被統治的人民完全知道真相,討論真相。所以他們才不敢冒險讓假牙公諸於世。因為我是臺灣人不像外省政治犯孤零零的,臺灣人至少還有一些親戚朋友同學人脈。媽媽當場看到真相反應激烈,如果判我死刑,媽媽一定會激動地拿著假牙當武器到處哭訴引發外界關注,況且臺灣人對二二八大屠殺的記憶猶新餘恨仍濃,馬上會勾起臺灣人集體悲憤的情緒,恐怕才是蔣家政權真正憂慮顧忌的。蔣介石父子當然深知在對岸有中共政權,國際情勢又不利下如果激起台灣人又像二二八事件那樣的反抗,蔣家政權就可能全面潰敗。蔣介石也不再只是一名魯莽大軍閥他曾統治過中國,他多少也會顧慮史家的鞭笞。而且特務這次一抓,就抓了她的三個兒子,如果再槍殺了她的兒子,絕對制止不了她的哀嚎,引起同情共鳴。畢竟蔣家統治集團在臺灣是絕對的少數,像南非的白人。顯然怕﹁真相﹂洩漏出去讓統治者屈居下風,不得已才跟媽媽協商?顯然統治者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也是我們這些年輕的反抗者,看似是在以卵擊石卻仍然敢于冒死反抗的思維邏輯之一。不反抗就是自願為奴,這是反抗者的信條。
今天的判決結果也讓我更清?地領悟到,統治者最擅用的就是製造恐懼所形成的懦弱,讓被統治者在自保下耽溺於屈服順從之中,而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揭露時所能激發出的人民的反抗意識和反抗精神。
獨裁政權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人民在恐懼下不敢公然反抗。在臺灣蔣介石集團所以會長期遂行恐怖統治,是因為它心存﹁流亡政權的報復心態﹂和﹁少數統治多數的恐懼心態﹂。但是任何會激起反抗精神的條件和因素,它也會小心翼翼地排除或避免。所以戒嚴時期的政治犯審判都採秘密方式進行,除非外界有壓力像雷震案以及多年後的美麗島事件。它敢處死那麼多人卻不敢正面碰觸一副假牙,因為它也害怕假牙捲起不可臆測的反抗精神和反抗意識。
挺身反抗,你才從奴隸變成人。
這一夜我獲得一個很珍貴的結論,影響我一生:獨裁者不可能堅強到完全沒有任何破綻,神樣無敵的阿基里斯都有脆弱的腳踝。反抗者如果有殉道的決志,機靈的智慧和堅定的反抗精神,特別是殉道的決志,總會逼得獨裁者也不得不有所讓步。獨裁者敢殺一個求饒的懦夫像殺一條狗,如果被迫必須和死士公然決鬥,獨裁者必定會猶豫迴避。因為死士失去的就是一條命而已,而殉道更是死士另一種型態的歷史性勝利。統治者呢?贏了勝之不武,若有閃失呢?這一點就是獨裁者的阿基里斯腱。
在反抗途中,怕死必死。
在台灣反抗運動史中,我一生三次該死未死就是因為我是死士。我次次都對準蔣介石父子的阿基里斯腱,並以生命下注。全口假牙這一張牌是首次出手,它給了我經驗也給了我信心。多年後在舉國皆曰可殺的恐怖氣氛下,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中的笑傲,侃侃又諤諤的雄辯,又是死士在叫陣。但是這一次他不是為了保命,而是決心捨命抓住國際及國內媒體充分報導的機會,企圖轉敗為勝,喚醒台灣人民的反抗意識,激勵台灣人民起來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捍衛主權……。
美麗島軍法大審那個死士不是一朝一夕誕生的,他是從這一階段就開始養成的。
監獄是反抗者的學校亦是煉鋼廠。
 圖片翻攝自施明德回憶錄《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
圖片翻攝自施明德回憶錄《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1962-1964)。
(施明德精神上的朋友如欲獲得這份珍藏贈品,請查閱「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網站,點選「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心存敵意者勿碰。)
- 【東京鐵男見聞】戰國第一武將真田幸村的故鄉 —上田
- 【完整菜單】小巨蛋美食+1!全新咖啡廳 pastaio noodle cafe 早午餐、下午茶通通有 極厚法式吐司、生義大利麵必吃
- 從台灣到美國 政治文化才是民主良窳的關鍵
- 台東紅烏龍茶飄香威尼斯「雲水之都」!攜手陳耀訓「紅烏龍義式麵包棒」限量開賣
- 國防部修訂「志願士兵甄選條件」的省思
- 收百萬元助王大陸造假病歷逃兵 3「兵役黃牛」遭聲押禁見
- Mister Donut 聯名珍煮丹!黑糖系甜甜圈甜蜜開賣、期間限定買 6 送 3
- 【有片】美國紐奧良退役美軍衝撞人群致15死 攜IS旗幟疑為「恐攻」有同黨
- 【獨家】台肥南港C4基地廢土案爆單據造假 北市府祭重懲開鍘:即日起勒令停工
熱門關鍵字
評論
世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箱:service@upmedia.mg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探索網站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e-mail:service@upmedia.mg
關注我們的報導社群
提供新聞:news@upmedia.mg
投書評論:editor@upmedia.mg
客戶服務:service@upmedia.mg
廣告合作:ad@upmedia.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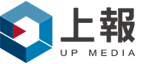

 32.6°C
32.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