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測試)【完整菜單】延長至五月底!添好運港式飲茶 100 分鐘點心吃到飽只要 699 元
2025-04-28 12:44 -
美日俄三巨頭如何瓜分世界是我們該擔憂的事
2025-02-22 07:00 -
廖偉棠專欄:《巴布·狄倫:搖滾詩人》──挑釁的傳主,不挑釁的傳記片
2025-02-22 07:00 -
台日菲防禦監控情資共享之必要與迫切
2025-02-22 07:00 -
為什麼川普不可能變獨裁
2025-02-21 07:00 -
國防部修訂「志願士兵甄選條件」的省思
2025-02-21 07:00 -
這樣的信徒不是在敬奉神明
2025-02-21 07:00 -
【大師講堂】抗中或成川普和莫迪「兄弟情」的催化劑
2025-02-21 07:00 -
從台灣到美國 政治文化才是民主良窳的關鍵
2025-02-21 00:00 -
「藍白敵人論」無法讓罷免運動成功
2025-02-20 07:01
《大家論壇》文學家視角:俄國8年前發動戰爭 2月24日進入地獄階段

拉斐言柯(Volodymyr Rafeyenko)
●烏克蘭作家
蕭爾(Marci Shore)
●耶魯大學副教授
烏克蘭小說家拉斐言柯(Vladimir Rafeenko/Volodymyr Rafeyenko)1969年出生於頓內次克,並以作家和俄文語言學教授的身分居住於此,直到2014年俄國力挺的分離主義份子讓頓巴斯陷入戰爭為止。逃至基輔郊外村落後,他用俄文撰寫了關於戰爭醜態荒謬的小說《白晝的長度》(The Length of Days),以及關於語言、流離失所和在祖國成為難民的烏克蘭文小說《空耳》(Mondegreen)。以下是他接受蕭爾的訪談,透過通信在2022年3月至4月進行,譯自俄文並經編刪以清楚呈現內容。
蕭爾:在演講和談話中,你多次談到「此時此地(Zdes’ i seichas),此時此地有必要成為人類」,如今這對你意謂什麼?
拉斐言柯:我目前的人生脈絡很明確:俄烏戰爭,一場俄國在8年前發動的戰爭,2月24日進入了地獄般的階段。到了現在,身而為人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與同胞同在,為了勝利盡己所能。
蕭爾:2月25日,入侵後的第2天,你寫信告訴我:「戰爭。真正的戰爭。」當時你人在哪?
拉斐言柯:戰爭開打時,我和妻子發現身處俄軍佔領區,我們被困一個多月,到了4月才奇蹟似地被志工救走。
蕭爾:俄軍士兵行徑如何?你和夫人有和他們交談嗎?
拉斐言柯:沒有,我們沒和他們交談。有什麼好談的?一點好處也沒——尤其是淪陷前幾天,我們聽說俄軍殺害附近村落的平民。一個我信得過的人告訴我,離我們不遠的村落有戶家庭被殺光光,小孩大人無一倖免,是卡德羅夫派(編按:kadyrovites,即效忠俄國的車臣戰士)下的手,只因這戶人家拒絕提供俄軍食物。
隨著時間過去,俄軍行為確實出現了變化——從溫和的法西斯變成了無法無天的法西斯。一開始他們希望快速拿下基輔時,並未系統性地緝捕平民,然而隨著我軍激烈抵抗,俄國原本的目標變得更難達到,俄軍行徑也變得更乖張。
志工帶我和妻子抵達檢查哨時,卡德羅夫派——在他們離開基輔前——有時會朝掛著白旗和寫著「兒童」的車輛開槍自娛,聽說他們會放一些人通過,有些則不放,都沒個準。
蕭爾:你怎麼逃出去的?
拉斐言柯:開戰第一天我們就設法逃出去,不過2月24日上午就已經行不通,戰車擋在我們和基輔之間,戰鬥非常激烈。當水電和網路被切斷,商家大門深鎖,狀況顯然會從很糟變得更糟時,我們找不到糧食,因此想盡辦法逃離。但人道走廊沒到我們那,自己也沒有交通工具,假如有的話起碼還能去可以轉運到基輔的地方。有車的人開始逃離村落,我們只能被迫留下,萬念俱灰時,我的朋友德瑞許找到了志工。這些人有勇有謀,想嘗試硬闖俄軍檢查哨。他們把我們湊在一起,然後從原路帶我們離開。第1次沒成功,我們萬念俱灰,但幾天後他們還是來了,這是我們8年來第2次撤離家園。就像第1次,我們拋下了所有家當,但當我們踏上烏克蘭土地,那開心真是言語難以形容。
蕭爾:我想到了阿赫瑪托娃《安魂曲》的序言: 在大清洗(1936-38)的可怕歲月中,我在列寧格勒監獄的等候隊伍中度過了 17 個月。有次,不知何故,有人「認出」了我。站在我身後的那個唇色鐵青的女人,從我們在場所有人特有的恍惚中醒來,當然,她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但她在我耳邊問我(那裡所有人都說耳語):
——你能把這些傳述出去嗎?
我說:——我可以。
阿赫瑪托娃的「我可以」確認了某種認識論上的樂觀主義,這種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所稱的「界線處境」(Grenzsituation),是否可用文字表達?
拉斐言柯:我和太太躲藏的屋子因為俄軍轟炸不斷震動,這期間我都有寫日記。要寫出文學筆觸幾乎不可能,但我可以、也有必要,把事件、當下狀態等等我所在地的重要資訊記錄下來。這讓我可以把注意力從無止盡的空襲和交火,轉移到我和妻子被迫離開故鄉頓內次克後住了好幾年的鄉間小屋周遭。我們放棄頓內次克的家,原因和我們放棄現在的棲身處沒有兩樣——俄國毀了我們的生活。
蕭爾:關於重要資訊:戰爭必定是具象和感官印象最鮮明的時刻,但矛盾的是,在這同時,形而上的東西也同樣鮮明:邪惡從何而來?彷彿實證與形而上之間的關係不知何故破裂了…
拉斐言柯:邪惡從何而來的問題我現在不太感興趣。有差嗎?重要的是能分辨善惡。在日以繼夜的轟炸之下,沒人會去想邪惡從何而來。沒錯,極其敏銳、害怕甚至恐懼的感覺是有,得和恐懼與恐慌搏鬥的實證經驗,是我人生至今,最歷歷在目、最可怕的時刻。
但形而上的東西確實離我很近,凝視並觸摸著我,我看到主之夏離我僅一步之遙。我知道死並不可怕,怕的是死得不漂亮。我請求上帝——如果我和妻子注定要死在鄉間小屋——賞我們一個痛快。
蕭爾:我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1939年,不過有網路——一切都看得到,赤裸裸地呈現,我們在即時觀看人們被殺。
拉斐言柯:戰爭正在這裡上演,一場意圖消滅烏克蘭人的戰爭。俄國人來消滅我們國家,消滅這群勇於選擇自我發展之路、和克里姆林宮帝國野心格格不入、有悖於俄國多數人民收復故土理念的人民。事實可怕的地方在於:絕大多數俄國人支持消滅烏克蘭人。戰場上俄國人毫不留情,佔領土地後手段殘暴,姦淫擄掠,殘殺婦孺,不論是馬立波或哈爾科夫,是切爾尼戈夫或蘇米,他們知道若某個地方屢攻不下,乾脆就放把火全部燒光。
蕭爾:邪惡與殘暴並不新奇,新奇的是網路能把一切都攤開在眼前——這是史上首次萬事如此透明。
拉斐言柯:是的,厲害的是當下的一切都涵蓋在這種透明度裡面,不能再把頭埋在沙裡假裝沒看到。假如你沒看到俄國暴行,不把俄國視為人類災難,你就是刻意沒看到,這樣一來你就是在善惡間做了選擇。
蕭爾:真理能拯救我們嗎?
拉斐言柯:我能肯定的是,人努力不脫離真理,就是在實現救贖。
蕭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3月對俄軍喊話:「如果你們向我軍投降,我們會給你們人應有的待遇——就是尊嚴,你們在軍中缺少的東西。」對我而言,這是個分水嶺,不僅提出交易,也確信了道德原則:我們不會變成像你們一樣。話說回來這種情況下很難不成為怪物,需要比大多數人花更多力氣。
拉斐言柯:西方世界得要知道,戰爭中有罪的不是普丁,他並沒有創造俄羅斯人,是俄羅斯人創造了普丁。他是他們的工具,另一個自我,不是錯覺,也不是為賦新辭強說愁,他就是俄國文化的肉身,而這頭野獸必須被阻止。
蕭爾:你認為現在有辦法接觸俄國人嗎?
拉斐言柯:我認為只有慘敗——可怕又空前的敗仗——加上苦澀的悔悟,才能讓俄國人清醒,讓他們重回現實——假如他們做得到。
蕭爾:關於俄國人,親近感也是個問題。我在想1941年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Jedwabne)發生的大屠殺:猶太人被他們的波蘭鄰居殺害,被他們以最熟悉名字稱呼的人屠殺。你在俄國也有讀者,來殺你的人口操你的語言,這種情況下,能對他們說什麼?當語言不再有效力……真的就沒橋梁了嗎?
拉斐言柯:本世紀初我把自己定位成烏克蘭作家,也活躍在俄國文化語言領域,我從沒想過用烏克蘭文寫作。2014年後,我學了烏克蘭文並用烏文寫了部小說,給俄國人和其他人看。就算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學烏文也不是問題——我的程度不但會說,還能出版文學作品。我在訪談中不止一次說過,那時起我會用兩種語文寫書——俄文及烏文小說。我很希望向每個人清楚表達,保衛烏克蘭境內俄語人口從來就不是問題——現在也不是,即便這正是俄軍從我祖國「解放」我和家人的口號。
我們被迫離開基輔,當然也知道俄國人不會善罷干休,的確也有後續。2月24日後,我下定決心不再發表任何俄文文章,我不要那些殺害烏克蘭兒童的禽獸來理解我,我對他們無話可說。還沒有一種語言是發明來讓你跟上門殺你全家老小、摧毀家園和焚燒土地的人交談。我不想再用俄文為烏克蘭文壇做出貢獻,就算間接也一樣,如果它還撐得下去,就讓它沒有我吧。
蕭爾:這也讓我感到非常難過:普丁不配說這種語言,你比他更值得說俄語,他永遠無法用這種語言做你的事,永遠無法像你那樣理解文豪契訶夫,你為何要為他放棄你的語言…
拉斐言柯:我就是無法再用俄文寫作,一想到有人會因為我用俄文寫作就以為我是俄國作家,這讓我難以忍受。
蕭爾:俄國入侵後不久,我和來自利維夫的普羅查斯柯(Jurko Prochasko)交談,有次我問他:「我還能為你做什麼?」他回答:「相信。」信念和信仰從何而來?
拉斐言柯:來自人類內心,來自升起並普照在善人與惡人的太陽,來自莎士比亞的著作和孩子的微笑,來自朋友的微笑和孩子的擁抱,來自入春的暖雨,來自我們頭頂蔚藍的天空。
(翻譯:鄭可妮,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riting Off Russi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世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箱:service@upmedia.mg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探索網站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e-mail:service@upmedia.mg
關注我們的報導社群
提供新聞:news@upmedia.mg
投書評論:editor@upmedia.mg
客戶服務:service@upmedia.mg
廣告合作:ad@upmedia.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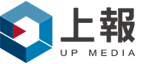

 30.2°C
30.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