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測試)【完整菜單】延長至五月底!添好運港式飲茶 100 分鐘點心吃到飽只要 699 元
2025-04-28 12:44 -
美日俄三巨頭如何瓜分世界是我們該擔憂的事
2025-02-22 07:00 -
廖偉棠專欄:《巴布·狄倫:搖滾詩人》──挑釁的傳主,不挑釁的傳記片
2025-02-22 07:00 -
台日菲防禦監控情資共享之必要與迫切
2025-02-22 07:00 -
為什麼川普不可能變獨裁
2025-02-21 07:00 -
國防部修訂「志願士兵甄選條件」的省思
2025-02-21 07:00 -
這樣的信徒不是在敬奉神明
2025-02-21 07:00 -
【大師講堂】抗中或成川普和莫迪「兄弟情」的催化劑
2025-02-21 07:00 -
從台灣到美國 政治文化才是民主良窳的關鍵
2025-02-21 00:00 -
「藍白敵人論」無法讓罷免運動成功
2025-02-20 07:01
【大師講堂】我們在敘利亞錯過了什麼? 一場漠然之後的激進崛起

沒有發生一場決定性的重大戰役,舊政權就像紙牌屋一樣倒塌,勝利歸於真正願意為自己的訴求戰鬥並犧牲的一方。
~歐洲高等學院哲學教授 齊澤克(Slavoj Žižek)
敘利亞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垮台,就連喬拉尼( Abu Mohammad al-Jolani)領導的「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為首的反對勢力也感到驚訝,這局勢也為各種陰謀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色列、土耳其、俄羅斯和美國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逆轉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俄羅斯並未以支持阿塞德的名義出手干預,是否真的因為它無法承受在烏克蘭戰場之外進行另一個軍事行動?還是背後存在什麼交易?美國是否會再次掉入支持伊斯蘭勢力對抗俄羅斯的陷阱,重蹈1980年代在阿富汗支持聖戰者的覆轍?以色列則做了什麼?它當然受益於世界轉移對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關注,它甚至在敘利亞南部為自己攻佔更多領土。
像大多數的評論員一樣,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這就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把焦點放在更宏觀的大局上。阿塞德政權垮台就像美國倉促撤出阿富汗後的局勢,或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勒維政權,這些事件的普遍特徵是,沒有發生一場決定性的重大戰役,舊政權就像紙牌屋一樣倒塌,勝利歸於真正願意為自己的訴求戰鬥並犧牲的一方。
阿塞德政權遭到普遍憎恨,這一點並不足以完全解釋它為什麼一夕垮台。為什麼世俗的反阿塞德勢力消失,只剩下穆斯林基本教義派趁勢崛起?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套用到阿富汗: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甘冒著生命危險搭上逃離喀布爾的班機,卻不願意為對抗神學士而戰?舊阿富汗政權的軍隊擁有更精良的裝備,但他們顯然並未全力投入對抗神學士的戰鬥。
 兩名敘利亞男童20日在大馬士革奧米亞大清真寺前跟反抗軍拍照。(美聯社)
兩名敘利亞男童20日在大馬士革奧米亞大清真寺前跟反抗軍拍照。(美聯社)
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1979年兩次訪問伊朗時,被一些類似的現象所吸引。他注意到,革命人士對自身生存表現出一種漠然的態度(亦即他們的行動並非為了求生存),這讓他印象深刻。對此,根據加梅茲(Patrick Gamez)的解釋,這些人「講述真相時,帶有鮮明的立場且充滿對抗的形式」,他們追求的是「透過鬥爭和磨難的方式改變現狀,不同於現代西方強權所採取的安撫、中立和規範等方式……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在於他們所採用的真理觀……這種真理是片面的,帶有立場的,只對特定立場的人士有意義。」
傅柯本人這樣說:
「……如果這個談論權利的主體(或權利本身這個主體)所說的是真理,那麼這種真理已不再是哲學家所謂的普遍真理……這種真理對整體的興趣,僅從片面的視角看待它、扭曲它、或單純根據自己的觀點審視整體。換言之,這種真理只從他們的戰鬥位置出發,從他們追求勝利的視角呈現真理,最後是(可以說是)從說話者主體本身的生存角度呈現的真理。」
外界是否可以批評這種「戰鬥式」觀點是「原始」落後的?因為這些社會尚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中強調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對於任何稍微熟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正如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eorg Lukacs)所言,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普遍真理性」,恰恰是因為它「偏向」某個特定的主觀立場。傅柯在伊朗觀察到的現象——呈現敵對(「戰鬥」)觀點的真理,這種片面式觀點的真理其實早就存在於馬克思思想中,他發現,參與階級鬥爭並不是獲得「客觀」歷史知識的障礙,反而是獲得「客觀」歷史知識(看清歷史真相)的先決條件。
實證主義的知識觀主張知識應該是「客觀 」呈現的現實——傅柯稱之為 「現代西方強權那種安撫、中立和規範化的形式」——是一種 「意識形態終結 」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我們擁有所謂超越意識形態的專家知識;另一方面,我們是被分散的個體,每個人都專注於自身特有的 「自我關懷」(care of the Self,傅柯的用語)——亦即能為個人生活帶來歡樂的小確幸。從這個自由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看,任何普遍性的承諾,尤其是需要冒著生命與肢體風險的承諾或行動,都是讓人起疑且「非理性」的。
這裡,我們碰到了一個有趣的悖論:傳統馬克思主義或許無法提供一個足具說服力的解釋,說明神學士為何會成功,但它確實幫助我們理解傅柯在伊朗看到的現象(以及我們在敘利亞應該關注的類似現象)。在全球資本主義勝利的影響下,民間集體行動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精神逐漸式微,因此傅柯希望能找到一個不依賴宗教基本主義就能動員集體參與的範例。然而,他沒有找到。
 阿富汗神學士戰士12日在東部帕克提亞省(Paktia)參加官員喪禮。(美聯社)
阿富汗神學士戰士12日在東部帕克提亞省(Paktia)參加官員喪禮。(美聯社)
對於當今為何宗教似乎在集體承諾與自我犧牲上占據壟斷地位,布登(Boris Buden)做出了最好的解釋。他認為宗教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反映了社會的後政治解體(post-political disintegration),亦即保證維持社會與群體穩定連結的傳統機制瓦解。宗教的基本教義派不僅是政治,它本身就是政治。對其信徒而言,它不再只是一種社會現象,而是社會的核心結構。
因此,現在已經無法區分宗教純粹的精神層面與政治層面之別:在一個後政治的世界,宗教成了重新號召不滿激情的管道。近期的發展顯示,宗教的基本教義派看似得勝,但這並不代表宗教重新回歸在政壇扮演要角,而是政治本身以一種新的形式回歸。
那麼問題是,世俗激進政治(這是歐洲現代性被遺忘的偉大成就)到底怎麼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由於它缺席,我們正接近組織化社會的末日──一旦到了這個不歸點,我們甚至沒有能力採取常識性的簡單措施,「避免對環境造成災難般的破壞」。儘管喬姆斯基聚焦在我們對環境的漠不關心,但我想將他的觀點擴展到我們普遍不願意參與的政治角力。為避免可預見的災難需要集體做出決定,這過程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政治過程。
西方的問題在於,它完全不願意為了一個偉大的共同目標而戰。舉例來說,那些希望無論用什麼條件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和平主義者」(peaceniks),說穿了是在捍衛他們舒適的生活,並準備好為此犧牲烏克蘭。義大利哲學家布拉迪( Franco Berardi) 說得對,我們正在目睹「西方世界的瓦解」。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歐洲高等學院哲學教授,倫敦大學伯貝克人文學院國際主任,著有《基督教無神論:如何成為真正的唯物主義者》(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暫譯)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 Did We Miss in Syri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延伸閱讀:
永慶房屋示警:房市交易平均每4件就有1件短期交易 買賣屋「貨比三家」有保障
「先誠實再成交」是真的! 永慶房屋推出獨家「誠實安心認證」保障消費者權益
房仲服務首重誠實與安心!永慶房屋真房價保證與三不政策 提供最完整保障

世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箱:service@upmedia.mg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探索網站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e-mail:service@upmedia.mg
關注我們的報導社群
提供新聞:news@upmedia.mg
投書評論:editor@upmedia.mg
客戶服務:service@upmedia.mg
廣告合作:ad@upmedia.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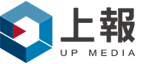

 32.6°C
32.6°C